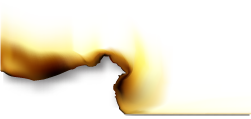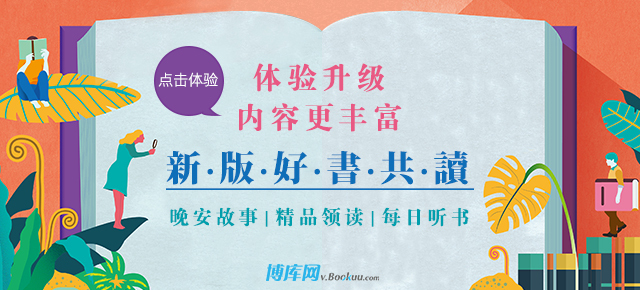编辑 | 博库小书
主播 | 留白时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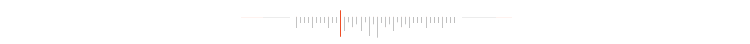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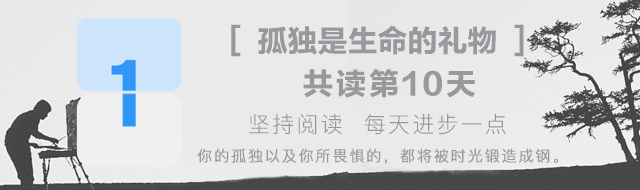
「 这 是 好 书 共 读 陪 你 共 读 的 第 54本 书 」
亲爱的好书共读栏目书友们,很高兴遇见你。
新版好书共读已上线
每晚20点,伴你共读好书
别忘了在随笔区写下读书心得哦
木心先生在《从前慢》中写道:
记得早先少年时/
大家诚诚恳恳/
说一句,是一句/
清早上火车站/
长街黑暗无行人/
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/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
车,马,邮件都慢/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/
从前的锁也好看/
钥匙精美有样子/你锁了/
人家就懂了/
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木心先生的故事。
下面开始今天的共读:最终章《木心三帖》
本次推荐阅读时间为20分钟左右,覆盖原书的第194页到第198页。

一个孤孤单单的人,却是真正的精神贵族。

出门前,从书架上抽出《琼美卡随想录》,带着木心去南京。闻说周日在乌镇将有一场追悼会,可惜我于周六便要赶回香港陪大女孩过圣诞,停留不了。而且想象中的木心应该不会渴望更不会稀罕谁去追悼他,但也不会坚决反对,他应是淡然恬然的,年轻时如斯,活到八十四岁了,更必如斯。
他在书里不是感叹过吗?“蒙田,最后还是请神父到床前来,我无法劝阻,相去四百年之遥的憾事。”可见他对生命风格的一致性看得颇重,尤其对生命尽头的操守,更重,所以在淡然恬然的木心的追悼会上如果大家又哭又号又叹又哀,他肯定摇头,不知道应该对朋友们说些什么。
有好长的时间误以为木心是“台湾作家”,因为一直在台湾报纸副刊上读他的文章,那时候,他在中国内地早就坐完牢了,远走美国,不归,不愿归,不愿归,但仍继续写作、画画和思考,文章刊登出来,八十年代,我是台大学生,每回读后都惆怅半天,连面对女朋友都说不出话来。
怎么说呢?木心在报上发表的大多是语录式的短散文,任何一句、两句、三句,是中年的他的个人感悟,却成为年轻的我的思考启发,似懂不懂,若虚还实,足够放在心头咀嚼半天。
是的,咀嚼,木心说过,“快乐是吞咽的,悲哀是咀嚼的;如果咀嚼快乐,会咀嚼出悲哀来”,那时候的我只觉这位英俊的作家很有玩弄字词的本领,唯有当活到某个年纪,才真明白他在说些什么,但到了那个年纪,欲辩已忘言。
是的,英俊,木心之于年轻的我的另一个吸引自是他的俊朗,脸部五官像雕刻出来的石像,笔挺,坚毅,另一个有着如斯脸容的中国作家是民国的邵洵美,美得令人舍不得不看却又不敢注视太久,怕会沉溺。邵洵美也像木心一样写诗,也画画,但前者有妻有情人,后者呢,据说是耽美界的同志,美得只爱属于他的性别的物种。之所以当木心谈及拜伦之死,意见是死得其所也死得其时,万一他鸡皮鹤发地活到老年,简直破坏西方文学史的美感。依此逻辑,木心其实活得已经够久够长,毕竟八十四岁了,老来又能回到故乡看山看水,老去,逝去,告别中国文学史,依然能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美感,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功绩与奇迹。
别了,木心,他写过,“如欲相见,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”。那就让我们去该地寻他,一定寻找得到,因为,谁都有悲喜交集,谁都逃不脱这生命的宿命。

在南京的演讲活动结束后,好些本来飞回北京的朋友都改变了计划,改往乌镇,出席木心先生的追悼会。他们问我去不去,我说香港有事,没法去,其实是在心里坚持那个想法,木心应该不会高兴朋友为他追悼些什么的,别打扰他了,虽然他已离开人间。
但又或者木心先生也不会反对朋友为他追悼,他是淡然得无所谓,自己的离世,朋友的哀伤,反正人间无秩序,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。
木心不是在《很好》文内写过吗?“昨天我和她坐在街头的喷泉边,五月的天气已很热了,刚买来的一袋樱桃也不好吃,我们抽着烟,‘应该少抽烟才对。’满街的人来来往往,她信口叹问:‘生命是什么呵?’我脱口答道:‘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。’”
既然不知道如何是好,那便做什么都好也或都不好。你想就去做吧,做什么都可以,只要自在如意。
木心眼中的“如意”是这样的:“集中于一个目的,做种种快乐的变化。或说,许多种变化着的快乐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了。”
木心如此定义快乐:“迎面一阵大风,灰沙吹进了西泽的眼皮和乞丐的眼皮。如果乞丐的眼皮里的灰沙先溶化,或先由泪水带出,他便清爽地看那西泽苦恼地揉眼皮,拭泪水。之前,之后,且不算,单算此一刻,乞丐比西泽如意。世上多的是比西泽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,在眼里没有灰沙的时日中,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,然而难以构成快乐。”
读木心的文章,感受到强烈的“境界”二字。他仿佛站在一个位子上,察看我们,而这个“我们”,理所当然地包括他自己。偶开天眼,红尘里,他亦是可怜的眼中人。
所以木心也曾说:“不幸中之幸中之不幸中之幸中之……谁能置身于这个规律之外。理既得,心随安,请坐,看戏(看自己的戏)。”
一位看戏的人走了,他从别人的戏里看出自己的戏,也从自己的戏里映照别人的戏,用文字记录下来,幕闭了,幸好仍有文字,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说说唱唱的痕。木心写过一篇《不绝》,开篇道:“一个半世纪彩声不绝,是为了一位法国智者说出一句很通俗的话:人格即风格。十八、十九世纪还是这样的真诚良善。”由是他抒发了一些关乎现代的感慨。
是的,除了境界,就是格。有格,木心告别中国,中国告别木心的格。

南京气温是零下三度,对我这来说,已是致命之寒,出门必须穿上男装丝裤。嗯,对了,南京之于北京,亦是“江南”,但彼“南”终究属于我们的“北”,至少在香港地区,没有“零下”这个可怕的概念。
于是穿上丝裤的我便很容易摆乌龙。好几次了,换装准备离开酒店房间,穿上大衣,伸手开门,无意间低头一看,始发现原来忘记穿外裤。假如没有这个“无意间”,往搭电梯,电梯门打开,站在里面的人恐必笑得弯腰流泪。
尴尬之事常有,有时候并非发生在自己身上,但作为旁观者,我也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像有一回,在男厕遇见其他部门的同事,站着聊了两分钟,离开时忽然看见他的裤裆湿了一大片,极明显,很可能是方便时不小心,或是洗手时被水龙头喷到而不自知,总之,难看,回到办公室时肯定惹笑。
于是我便非常挣扎,不知道是否应该提醒他。想说,但说不出口,不希望看他在我眼前显现窘态;不提醒,又好像眼睁睁看着他稍后出丑,等于看见别人快堕进陷阱而不阻拦。
结果我是保持沉默。自我安慰,说不定他直接回到房间,不会遇见任何人,何苦要我把糗事揭穿。我向来是个短视的人,只顾眼前一刻的快乐如意,日后的愁,管他的,日后再说了。
所以我很容易感动于一些好心地的人,自己做不到,唯有羡慕的份儿。
像在办公室看见男同事的西装肩上满布头皮,我通常懒得提醒,但当看见有其他同事提醒他,我便忍不住在心里暗道,呀,这是一个好人,我们的办公室毕竟有好人。
然而说到底,我对好人的欣赏感动依然远低于我对诗人的崇拜仰慕,如这两天说了又说的木心先生。他的诗,他的情诗,令人根本忘记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,在文字面前,好坏让路,最重要的是时间能够凝固于美丽的瞬间。像他说:
十五年前/
阴凉的晨/
恍恍惚惚/
清晰的诀别/
每夜,梦中的你/梦中是你/
与枕俱醒/
觉得不是你/
另一些人/
扮演你入我梦中/
哪有你,你这样好/
哪有你这样你 /
因为木心去世的缘故,因为圣诞新年交替的缘故,我重读了《我纷纷的情欲》书里的一些诗,在旅途中,读得恍恍惚惚,在飞机上,缓缓睡去。醒来时香港已在脚下,你在家里,我或许也在你的梦里。

好了书友们,到今天为止《孤独是生命的礼物》这本书已经带领大家读完了。
孤独是生命的礼物,孤独是对生命的敬重。罗曼罗兰说,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体会到孤独之后,便会真正的理解生命的意义。
下一期,我们将带领大家再一次走进东野圭吾笔下的悬疑世界:
畅销书作家在出国的前一晚于家中被杀。
凶手很快落网,对罪行供认不讳、但求速死,却对作案动机语焉不详。
他当真是罪犯?
他究竟为何杀人?
《恶意》这本书与《白夜行》恰似两生花,《白夜行》中的爱情极度炽烈,令人粉身碎骨;《恶意》中的怨恨则无比深沉,令人万劫不复。
敬请期待!
晚安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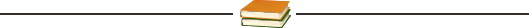
觉得文章有益
不妨点赞鼓励
也可分享给身边的书友
本期主播:留白时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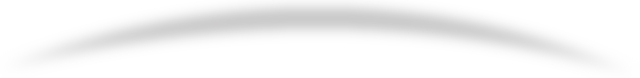
让生命自然而然流淌,活出最真实的自己。
一枚唯美&理想主义者,愿用声音温暖彼此的心灵。
荔枝电台:FM1653983
个人微信:liubai_buyi